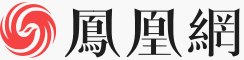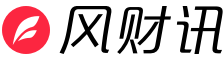在荒漠治理中,为了要能够防风固沙,需要有一种被称为“先行者”的植物。它们的根系要能够深深扎进沙层,穿过沙石的缝隙,汲取水分和营养,顽强生长下来,为后续的生态系统建立打下基础——它们被治沙的科学家叫做“先锋植物”。
丹桂飘香时节,孟延春副教授前来凤凰网演播室做客时,欣然提起了这类植物。不过,他并非治沙方面的专家,身份则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更新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他把城市更新中频繁出现的“网红打卡地”,比作城市更新的“先锋产品”。他说,要让人和新兴业态在一个地方扎得住根,就先要营造基本的生态环境。
“网红打卡地,就像先锋植物那样,城市与社区要借着这股旺盛的势头,去拓展更深、更广的产业结构体系,为城市迭代发展奠定更深刻的基础。”孟延春如是说。
从增量到存量:要做好“绣花”功夫
回顾城市更新的历史,是与过去四十年中国房地产同步发展的一部“更新”史。
城市更新的发展演进历经了从萌芽、起步、探索到提速四个重要时期,逐步形成了面向城市更新的系统化更新政策体系。
孟延春指出,城市的产业、建筑,有它的发展生命周期。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市的发展以增量型为主,大规模建设、大规模开发。进入21世纪,很多城市面临危旧房、棚户区、旧厂区、工矿区等改造,这种改造初期也是以大规模拆建更新为主要特征。到了现在,城市的规模扩张已经到了一个相对饱和的阶段,城市的发展需要更多存量的更新。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存量空间我们要精耕细作,要做好‘绣花’功夫。”
孟延春说,这就需要分三大块结构,有政府和政府的机制,市场和企业的机制,还有包括市民社会的机制。政府做顶层设计,企业发挥市场主体作用,社会层面建立市民机制。
政策层面,8月31日,住建部官网公布了《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明确积极稳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坚持“留改拆”并举,凸显对公共配套服务的诉求,政府层面对城市更新的社会价值考虑超越了市场价值。
在孟延春看来,一个城市要健康发展,应该是一种稳定的、逐步的、有序的更新,而不是运动式的大拆大建。在城市更新当中,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更新行动,它应该和城市发展的整体结合在一起。
城市文脉是一座金矿
城市更新除了避免大拆大建,更重要还在于保护和发扬城市文脉。
孟延春表示,“城市文脉和城市更新不是一个矛盾体,城市文脉本身就是城市更新当中需要挖掘的一个金矿。”
上述“绣花式”的城市更新,应该完全融入到城市当中,旧有传统文化的挖掘和城市历史的挖掘,恰恰体现了城市的文化特色。
在孟延春看来,网红打卡地的出现,就是与城市文脉相结合的重点布局,是避免每个城市千篇一律的结构体系。
以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波士顿为例,波士顿通过在区域内建立“创新创业生态”,把握年轻人的需求,为人才“定制生活”,形成了生活与工作多元无缝链接的活力社区,使南湾与肯德尔广场成功“变身”,在成为波士顿科技发展引擎的同时,成为了科技创新区崛起的模版。
孟延春指出,波士顿并没有提供便宜的土地,也没有给予减免税待遇,而是提供相应的生活服务设施。在规划之前,先判断这类产业人群有哪些特点,再提供什么样的住房,以及相应的生活、服务和基础设施、文化设施。等新区建好以后,自然而然就把那些人吸引过来了,相应的产业和业态也就进驻了。
“我们不能仅仅用网红打卡的方式让人们简单去看,拍拍照片、喝喝饮料,而是要借助其聚焦人气的气势,将人才留下来、将产业导进来。”
孟延春认为,政府在做区域规划时,应该首先有定位,有了定位以后,对这个地方要集聚什么样的人才,形成什么样的人力资源结构,提前有一定的判断。
此外,一个城市的发展,越能给外部区域提供更多服务,则其发展潜力越大。“如果一个城市只是服务于城市本身,这个城市是没有潜力的,是可能衰落的。它一定是能辐射更大区域,有长期的文化运营策略,才能得到长足发展。”
激励机制势在必行
城市更新箭在弦上,难点也显而易见。成本越来越高,利润空间越来越少,那么成本和效益如何平衡?
孟延春指出,在诸多城市更新项目中,有的项目公益性较强,有的是市场性较强,就要对不同项目有一定的剥离。偏市场性的,我们交给市场去做充分的市场竞争;偏公益性的项目,政府则要采取一些激励措施。
从经济学的理论上来说,在这类偏公益性的项目上,政府就要给予一些积极的激励机制,可能是通过税收的减免,或者是通过给予补贴来推动。
“在这个过程中,过去规模化、工业化的经营方式可能就不现实了,更多是要采用一种个性化、特色化的运营模式,这些都是城市更新的难题。”孟延春举例来说,“比如改造老旧小区,它本身密度大,改善难度就很大。这就要通过它的公益性和市场性的属性比重,来进行类型的划分。”
那么,应该有哪些激励机制?孟延春认为,可以设立相应的投融资机制,比如设立城市更新基金。“城市更新,它也是一种长期的行为。未来城市更新基金应该是长期存在的一种新的金融类产品。”
呼吁:城市更新项目应有“终结机制”
孟延春指出,目前城市更新项目没有明确的终结机制,也是面临的一大难题。“城市更新之所以归于公共管理的类别当中,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要与居民沟通,涉及利益的平衡,那么最终需要达成共识。”事实上,很难达成100%的共识,当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冲突时,“终结”解决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以《上海市城市更新条例》为例,上海市提出公有旧住房签约比例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协议方可生效。当然要根据城市更新项目公益性属性避免“多数人对少数人强迫”的现象,这就需要从法律上提供依据和支撑。
孟延春提到著名的日本成田机场,当时有一部分居民不愿意搬迁,法律上没有解决机制,那么在建机场时,只能在机场的夹缝中留下一片居民区,这显然对居民生活和机场运行都无益处。
孟延春副教授呼吁,目前国内没有形成统一的项目终结机制,从国家层面应该要有一些指导性意见。在现有框架下,既要有国家的顶层设计,也要有对城市的顶层设计,对不同城市来说建议有一个分权的过程以有利于城市更新项目的实施。
 我来说两句
我来说两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