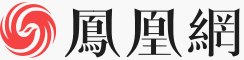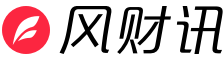“2023年全球平均城镇化率为57.3%,发达国家普遍超过80%,如美国83%、日本92%。我国的名义城镇化率为67%,看起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实际城镇化率只有48.8%,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日前,原国家房改课题组组长、原中房集团董事长孟晓苏在接受凤凰网《问渠人物》采访时表示,唯有打破户籍与土地的双重制度枷锁,才能将几亿农民从贫困的历史循环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能同城镇居民一起,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走向共同富裕的未来,并为中国经济注入持续发展的动力。
以下为部分采访实录:
问渠人物:过去常说,“要富裕农民就必须减少农民,要发展农村就必须繁荣城市”。在城镇化率发展到当下水平时,是否依然适用?
孟晓苏:这句话是八十年代农村工作部门的共识。中国农民要过上富裕的生活,发展城市化或称为“城镇化”就是不得不走的道路。这在当下仍然如此,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我国人均耕地匮乏,这也是农民贫困的结构性根源。
我国存在着全球对比下的人均耕地危机。中国耕地总面积约1.33 亿公顷,即20亿亩,占全球耕地的9.4%,但人均耕地仅为0.12公顷,即1.43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在世界126个国家中排名末尾。加拿大、美国人均耕地分别为中国的18倍和5倍以上,连印度亦为我国人均耕地的1.2倍。这是中国实际存在的国情。
目前我国有限土地的承载力已达到极限。在我国每公顷耕地需养活12人,远超全球均值约4人/公顷,土地生产力已逼近生态红线。这就造成土地质量劣化加剧。我国35%的耕地为低产田,是盐碱化、水土流失的劣质土壤。为增加单位产量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加重了对地力的掠夺与破坏。
1978年我国总人口为 10亿人,城镇化率只有17.9%,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多达8.2亿人。农业人口众多是多年不发展城镇化、畏惧发展城镇化所造成的后果。如今虽然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人口总量增长了,农村户籍人口仍占总人口的51.2%,即7.2亿农村人口。2023年全球平均城镇化率为 57.3%,发达国家普遍超过80%,如美国83%、日本92%。我国的名义城镇化率为67%,看起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实际城镇化率只有48.8%,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问渠人物:户籍制度在城镇化进程中起到哪些作用?
孟晓苏:建国初期,我国为应对战乱的国际环境,不得不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并推出配套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1953年起国家实施“以农补工”,通过廉价收购农作物与高价出售农用物资,营造出农村补贴城市、农业补贴工业的“剪刀差”。
1957年工业生产需要,农民进城人口达到2000万人,对城市供应体系形成冲击,让当时的城市管理者不能承受。1958年我国出台的《户口登记条例》,就是为维护当时的城市供应体系,严格限制农村人口迁进城镇而发布的。1960年起,又将部分城市居民“下放”到农村,以化解城市供应体系遇到的难关。
此次从“城乡二元结构”演变为“城乡二元制度”:户籍制度是一种人们与生俱来就被绑定身份的制度,分为农业户和非农业户,用它绑定粮票、住房、教育等有限资源的供应。城市居民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基本生活保障,占到财政支出30%以上。而广大农民群众却被排除在基本保障之外,理由就是他们有耕地和房屋,国家不必保障他们的生活。
这种制度在国家初创时期有短期的合理性,并取得了一定成果。1958—1978年,农业部门为工业部门提供的积累占比达到GDP的20%,农民群众用辛苦付出支持我国建成独立的工业体系。
这种制度能加强政府的管理功能。在物资普遍匮乏年代,通过制度把农业人口固定在农村,能维持城市的基本稳定。
问渠人物:延续至今的户籍制度,如何平衡“限制”与“发展”的关系?
孟晓苏:2024年户籍城镇化率48.8%,与常住城镇化率67%相差18个百分点,2.97亿农民工和农村留守儿童无法市民化。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仅为城镇职工的60%。
城乡分割的教育制度让国家长期发展受阻。来自农村的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平均为9.8年,低于城镇职工的平均11.3年,难以支撑技术密集型产业。目前城镇教育资源比较丰富,但是却用考试制度限制住农民工子女,让他们无法在城镇接受教育。
可以说,户籍制度的社会代价,已经从“不得已”成为了“发展枷锁”。
内需不足的结构性矛盾,对消费需求产生抑制效应。未落户的农民工边际消费倾向仅0.38,远低于市民的0.65。若户籍人口差距缩小能10个百分点,可释放消费需求约2万亿元。还造成政府财政资 源配置低效化。按户籍人口配置公共服务,导致人口流入地(如东莞)的医疗、教育资源紧张短缺,而流出地的设施空置率超过40%。
另外,农村建设用地浪费与城市用地紧缺并存。农村常住人口减少了40%,但宅基地面积反而增加了10%。严控宅基地向城镇居民转让的制度,正在加剧土地资源浪费与违背农民意愿状况的发展,造成多达3.29亿亩农村建设用地特别是宅基地处于半闲置状态,而目前城镇建设用地总面积是1.55亿亩,农村建设用地是城镇建设用地的2.12倍。随着城镇化进程与“半城镇化”逐步坐实,会有越来越多的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居住。
问渠人物:在您看来,目前户籍束缚与土地困局应该如何突围?国际上有哪些可借鉴的案例?
孟晓苏:应该吸取拉美国家的教训,避免“中等城镇化陷阱”。比如巴西的城镇化率达到86%,但缺乏住房保障使贫民窟人口占到1/4。公共服务缺位导致社会问题丛生。要学习德国榜样。德国通过《空间规划法》推行保障房等公共服务均等,即使在小镇也配备完善学校与医院,让农民进城无后顾之忧。
土地规模化经营才能释放剩余。以我国的情况,只有当农业人口更多转移到城镇生活工作,促进土地向种田大户或农场集中,让耕农户均耕地扩至50亩以上,务农的收入水平才可接近城镇就业的收入水平。
中国户籍制度诞生于经济匮乏下的工业化原始积累困境,其短期合理性不能掩盖制度性弊端:它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民陷入“耕地内卷—低效生产—贫困循环”的陷阱,并阻碍劳动力优化配置与消费升级。这种在计划经济下产生的特殊制度,是在旧中国都没有过的,在其它前社会主义国家中也是另类。
厉以宁教授曾经举电视剧《闯关东》为例,他说山东农民闯关东到了东北,可以在城里建房、买房、开店,生下孩子就是城里的人口;他们愿意种地、愿意住在农村也可以。在城里居住的可以搬到农村,在农村居住的也可以搬到城市。“可见那时有二元结构存在,却没有二元结构制度”。厉以宁指出:“建国后户籍制度被一分为二变成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导致生产要素的割裂,城乡之间的流动受到极大限制。这个难题不取消,我们就与市场经济有不小距离”。
唯有打破户籍与土地的双重制度枷锁,才能将几亿农民从贫困的历史循环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能同城镇居民一起,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走向共同富裕的未来,并为中国经济注入持续发展的动力。
 我来说两句
我来说两句